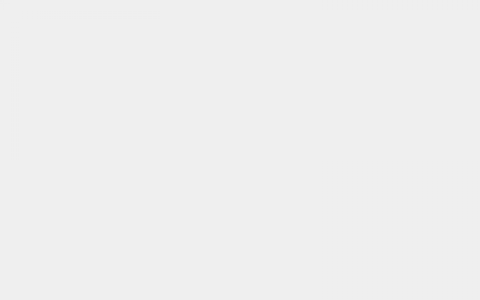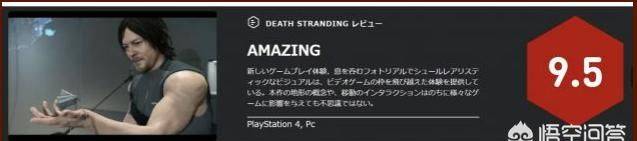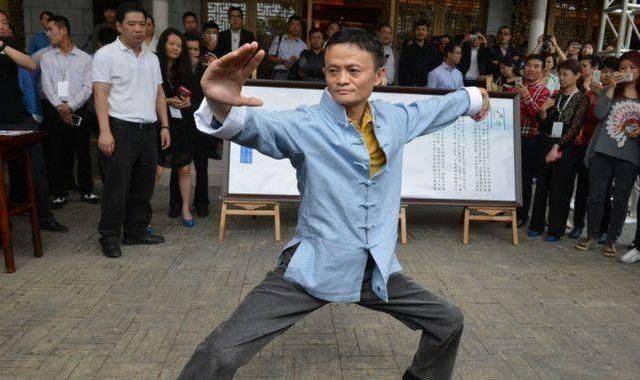因为历史是文人写的,宋仁宗礼贤下士,重视人才,尊重文人,文人士大夫是地主阶层,拥有话语权,而底层的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即使他们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他们也无处投告无人记录,但凡有口饭吃他们就不会揭竿而起。
从个人私德和对自己权力的克制上,宋仁宗配的上“明君”二字;但从执政能力上来说,他不够“明”,他只是个和稀泥的“老好人”。
他得到“仁”这个谥号是因为他真的很“仁慈”:对待大臣他很能纳谏,包拯的唾沫星子喷他脸上他都能忍;对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仁慈,回宫路上口渴了却不忍向宫人要水喝,因为观察到负责茶水的随侍不在,怕他要了茶水值班的人会受到责罚;对待百姓减徭役,遇到天灾设置救济所,找不到天灾原因就下罪己诏,一批一批的遣散宫人;对待造成他与亲生母亲分离且长期把持朝政不给他权力的章献明肃皇后,在其死后仍维护其名声,没有反攻倒算。
宋太祖坐上宝座后搞了个“杯酒释兵权”,宋太宗继位时搞了个“烛影斧声”,前两任皇帝的个人经历使得他们对兵权都特别忌惮,既要抵御契丹人和党项人的侵扰,又不想让军队坐大有太多话语权,他们不约而同实行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军队实力不行干不翻敌人,那就用金钱来交换和平,宋真宗与辽签了“檀渊之盟”,宋仁宗与西夏达成“庆历合议”。
随着几十年的相对和平发展,北宋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但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和冗费)在仁宗朝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对于国家财政危机,仁宗避无可避。他采用了范仲淹的十条改革建议开展“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核心想大干一场,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范仲淹、韩琪、富弼是新政领导小组,欧阳修、蔡襄等谏官为新政敲边鼓,但改革触犯了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他们攻讦范仲淹结党营私,有一次仁宗问范仲淹对朋党的看法,范仲淹就以君子党和小人党答之,主张天子要明辨君子与小人,欧阳修随后充当了猪队友,写了著名的《朋党论》对做了更深入的阐述,但却起到了反效果,因为他们没有把握好皇帝心理,皇帝最忌惮的是出现威胁皇权的势力,在皇权面前,什么财政危机、百姓疾苦都可以缓一缓,不管你怎么刷新“朋党”的概念,面对汉唐朋党乱政的先例都显的没有说服力。反对派耍了个手段诬陷他们要把皇帝拉下马,宋仁宗虽不信,但改革的决心动摇了。
一年后,范仲淹这帮改革派先后被排挤出京,庆历新政的各项措施被废除。宋仁宗虽看到问题,但他解决不了问题,就把问题搁置起来,他就像我们生活中的“老好人”,耳根子软,无原则,谁喊的声音大他就抚慰谁,只求眼前清净。他后来又把新政大臣召回,他的治国政策始终摇摆不定,朝令夕改,反反复复,帝国的隐忧他可以无视,作为皇帝,他胸无大志,缺乏魄力,面对谏官有时甚至显得软弱,有点窝囊。后期他最关心的是他能安稳的坐好他的位置,直到老去。
所以,说他是“仁君”没有争议,说他是“明君”就看跟谁比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里排个儿,他还算个不错的皇帝。